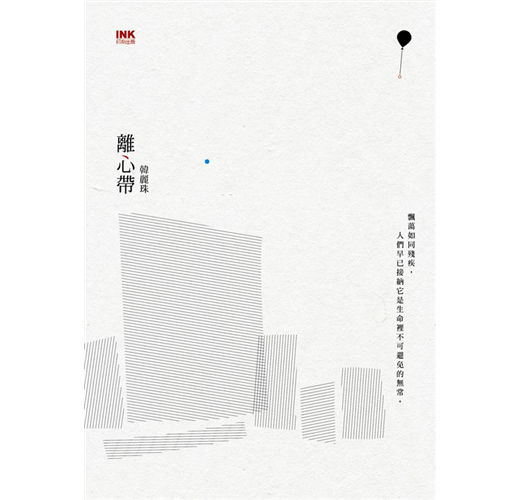飄蕩如同殘疾,人們早已接納它是生命裡不可避免的無常。
飄蕩症
最初,只是善忘。無法被緊記的事情像皮屑那樣紛紛脫落。
判別事物的準則變得不確定,方向感出現障礙,有時甚至不知道,想要走的路究竟在哪裡。
身體愈來愈輕,雖然重量並沒有一點改變,內裡一些重要的東西,那用以維持平衡和重心的元素,正在一點一點地流失。
四周的人的臉面,輪廓仍然相同,卻逐漸遙遠。
某一刻,身體終於不受控制地飄起來。
街道依然繁華,高聳建築、黑壓壓人潮、燈柱、老樹,以及被大廈切割成細碎小塊的天空,只是城市逐漸增設各種欄杆、粗麻繩與拒馬,以防人們突來的飄升,需要抓緊什麼來穩住身子。賣氣球的男人接起電話,一個進入飄蕩期的女病者前來求助,而他需以魚絲牽引她行進的方向。
母親失蹤,更多年以前父親在她母親面前飄走,執法者上門搜掠她的屋子,「尋人」取代驅逐攤販成為新的任務,於是她開始朗讀母親的筆記,試圖搜尋線索與氣味:「他們早已知道,對於某些人來說,肉身既沉重,也過分具體和實在,尤其在精神低落的時刻,令人分外難以承擔,只得尋求各種方法,像呼出一口氣那樣,放掉它。」
故事裡,目睹丈夫飄遠的妻子、遺失母親的女兒、眼底飛出黑影的攝影師、黑影爬上臉皮的女人,以及遺失了名字的白日癱瘓者,在不斷上升或癱軟的引力中,飄浮著。
作者簡介:
韓麗珠
一九七八年生於香港,十多歲開始寫作。著有《縫身》、《灰花》、《風箏家族》、《輸水管森林》、《寧靜的獸》以及《雙城辭典1.2》(與謝曉虹合著)、《Hard Copies》(合集)等書。曾獲二〇〇八《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二〇〇八及二〇〇九《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第二十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長篇小說《灰花》獲第十三屆紅樓夢文學獎推薦獎。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齊心推薦:
韓麗珠的小說一貫以超寫實的奇想吸引我們閱讀的興味,但卻毫不晦澀,讓人清楚感受到那與我們日常關切的貼近合拍與富含洞見,就像是眼睜睜看著夢境中的自己,那樣的詭異與投入。她新的長篇《離心帶》除了沿襲這樣引人的風格,還隱隱約指向某種之上與之外的超脫路徑,所以瑰奇觀照現實的同時,更見一種精神深度的啟發,值得讀者細細品味、好好思索。──朱偉誠(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Sigur Rós的主唱Jónsi一把獨特的嗓音教人繃緊又著迷,他使用冰島語演唱,或者根本是無法被翻譯的自創語言。演唱會上,Jónsi握持大提琴琴弓演奏電吉他,當他凝神刮著弦,那態勢,猶如宰殺一頭束手就擒的獸,然而其中又有一小段特殊聲響的展現,聆聽專輯時,以為用效果器處理過,沒想到現場他只是將電吉他湊進唇間(像吻著獸的身體),隔亙在他與麥克風之間,使電吉他成為一堵會發聲的牆(或者井),那夢幻的聲線便即席吟唱出來了。
韓麗珠的小說,讓我想起Sigur Rós。那裡面有不曾被誰給擁有的東西。──孫梓評(詩人、作家)
從《風箏家族》到《離心帶》,韓麗珠總是以高度的想像力,為人的存在問題,賦予了迷人的文學形式。出入於個人與群體之間,是離心,還是向心?要自由,還是束縛?無論是氣球、鏡子,還是「飄蕩症」,都充滿了象徵喻意,探詢著人與自我、與他人的相互關係,以及存在處境的種種問題,耐人品味。──梅家玲(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沒有人能預計飄蕩在哪一個階段突然出現,
有些人在青春期結束以後發現自己的身子頻繁地陷入了失重的狀況,
有些人在辭退一份工作或轉換一個伴侶之後的某個黃昏,忽然飄到半空,
有些人在安穩而重複的生活裡,雙腳便毫無先兆地離開了地面……
名人推薦:齊心推薦:
韓麗珠的小說一貫以超寫實的奇想吸引我們閱讀的興味,但卻毫不晦澀,讓人清楚感受到那與我們日常關切的貼近合拍與富含洞見,就像是眼睜睜看著夢境中的自己,那樣的詭異與投入。她新的長篇《離心帶》除了沿襲這樣引人的風格,還隱隱約指向某種之上與之外的超脫路徑,所以瑰奇觀照現實的同時,更見一種精神深度的啟發,值得讀者細細品味、好好思索。──朱偉誠(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Sigur Rós的主唱Jónsi一把獨特的嗓音教人繃緊又著迷,他使用冰島語演唱,或者根本是無法被翻譯的自創語言。演唱會上,Jónsi握持...
章節試閱
飄蕩
街道仍然繁華,像一鍋煮沸過久的開水,已經容不下任何多餘的事物。賣氣球的男人常常在正午把頭探出陽台俯視著街上密密麻麻緩緩蠕動的黑色頭顱,總是感到街道在離他太遠的地方。他可以想像,在那裡,人們已經習慣了自己的身子,被擠壓在眾多陌生而黏膩的肉體之間,當他們抬起頭,發現天空被高聳的建築物切割成細碎的小塊時,並不會感到驚訝,他們更不會介意,再也沒有任何鮮豔的氣球,偶爾在上空飄過。然而總有一些什麼,會阻止賣氣球的男人隨著想像逸出那工作室的軌道。例如頻繁地響起的電話,他並不樂意拾起那聽筒,他知道,
張開嘴巴,對著那聽筒說話的,是一個令他感到不以為然的自己。
那天,電話的另一端是一把乾巴巴的聲音,他知道那是凡。他不會忘記,那些在氣球工廠不分晝夜地加班的日子,凡總是在他身旁咳嗽。
工廠倒閉了以後的某天,他收到凡的來電,以社會福利部職員的身分,向他提出合作的建議,那時候,他要求賣氣球的男人,以姓氏對他作出尊稱。
「大約在下午五時,一位剛剛進入飄蕩期的女病患會按你的門鈴。」他這樣告訴賣氣球的男人,就像以往每一次,這是由醫院轉介的無望治癒個案。
「疾病的名目,快要比病患更多了。」賣氣球的男人忍不住抱怨。
「而你要做的工作只是,給他們提供希望。」社會福利部職員以一種嚴肅的語氣提示他。賣氣球的男人無法說出任何話,他只是感到胸腹間積聚了大量令他疼痛的氣體。誰都知道,販賣氣球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維持日常開支。要是病患不再向社會福利部求助,他將會得到一筆為數可觀的報酬。社會福利部的職員早已多次向他暗示,大部分的求助者,無法終止申請援助,歸根究柢,無非是沮喪,那是許多不治之症、虐待、酗酒、失業、被遺棄的主要原因。
掛斷了電話之後,鬱悶的情緒把賣氣球男人的視線引領到窗外,那片被灰塵遮蔽了的天空,他認為,女病患即將來電,而他會在電話中指示她從醫院走到氣球店的路︰「你會看見三個不同顏色的交通燈,但不要按照它的指引走到對面,而是向左拐彎,一直走,不久,你將會看見懸掛著藍色氫氣球的陽台。」他會告訴那女人,小心提防在街上徘徊不去的狗︰「不要看進牠們的眼睛裡,以免挑起牠們的憤怒。」但那氣若游絲的女人其實更擔心的是躲在燈柱或老榕樹後的不法之徒。「據說他們喜歡以身形瘦削,腳步虛浮的人作目標。」女人虛弱的聲音如此傾訴。「但真正的惡魔其實住在你心裡,」他打算這樣建議女人︰「嘗試跟它和諧共處,使它無暇牽引災害。」他對於自己的答案感到非常滿意。
當四個滾動中的輪子被拖曳在走廊凹凸不平的水泥路面,發出的聲音跟一列行駛中的老舊火車非常相近,賣氣球的男人轉過頭去,發現一只碩大而殘破的黑色皮箱,附著一個纖幼的女人,已經抵達了敞開的門前。那女人穿著一襲白色的裙子,蒼白臉面和手臂像一塊有待填上色彩和線條的宣紙。那使他想到,許多年前,他親自製作了一只白色的氣球,他把氣球啣在嘴巴,鼓起腮幫,把肺部的氣奮力吹進去,那氣球漸漸膨脹,橡皮膜呈半透明,成了一顆晶瑩飽滿的圓球,像一個人剛剛醒過來的臉。
女人喘著氣,還來不及說出第一句話,賣氣球男人的臉上已經蕩漾著模糊的微笑,他彷彿再次嘗到殘留在嘴唇的乾澀。
*
阿鳥感到自己的記憶像塗抹過久的油漆正在逐片剝落。她當然已經無法再想起已經遺忘了的事,而剩下來的卻愈發清晰起來,使她憂慮,那即將成為她人格裡不可或缺的部分。
當她閉上眼睛,腦子裡便會出現那些異常明亮的下午,天空清朗得幾乎無法找到任何雲層,她抑止不了盯著高空的衝動,雖然陽光非常刺目,但那並不妨礙她的期待,直至她看到本來澄澈的湛藍,不規則地分布著彩色小點,他們正在移動,而且愈縮愈小,那時候,她已經過了把彩色小點誤作風箏或飛機的年紀,但她還是希望跟某個人作出討論,於是她高聲問母親︰「他們在做什麼?」
阿了會走到她的身旁,以跟她相若的角度仰著頭顱,凝視那一片他們仍然無法完全適應的風景。其實那幾個人還沒有飄到太遠,只是稍稍高於最高的那幢大廈的上方。她似乎看到,他們已把身子放軟,彷彿逐漸順從了各種無法理解也難以抵抗的安排,但也有可能,這只是她理所當然的想像,畢竟,他們的身影也正在遠離她們的視線範圍。
「沒什麼。」阿了說︰「他們只是前往那個真正屬於他們的方向。」可是阿鳥就像並不滿意這種說法那樣,仍然頑強地盯著那片已經什麼也沒有的天空,直至眼前成了一片灰黑。很可能,那是眼睛長時間注視強光引致的後果,也有可能,那是阿了寬厚的手掌,而她的眼睛總是會流出被光刺痛的淚水。當她的視野慢慢復原,阿了便會告誡她︰「只要不把目光放在遙不可及的地方,便不會被其實並不存在的恐懼打擾。」阿鳥知道,那恐懼並不在屋子以外的地方,那一直在她們心裡。無論任何事物,一旦過於接近,人們便會輕易忽略它。
阿了總是容易忘掉自己說過的話,因此她反覆向阿鳥說明,她的父親如何被突發性的飄蕩帶走。「但沒有任何人能圓滿地解釋,帶走他的是一陣怪風,還是身體上潛伏已久的徵狀。」阿鳥記得她轉過來的臉,總是有一雙空洞的眼睛,使她認為,她的母親應該也在某個地方丟失了,而且每一次的說明都像第一次那樣鮮明而深刻,使阿鳥找不到任何空隙,細想自己是否已經感到煩厭。「絕對沒有任何先兆。」阿了無法抑止抱怨,她認為,要是徵兆更早出現,他們便有足夠的時間想到應付的方法,而她更難以釋懷的是,由於無跡可尋,當她嘗試搜索他離去前的回憶,發現那些日子,全都像大量複製的物品一般,欠缺可供記認的座標。
「他說,他感到很冷。」她只記得,那天有和煦的陽光,屋外的空地,到處都放滿了人們晾曬的棉被。她走進廚房煮了一壺咖啡,讓他暖和冰冷的身軀。「不過是一陣子之間的事情。他說,室內的空氣不流通,他感到呼吸不了,要到外面去,待一會兒。」她看著燒水的鍋子,很快,狹小的廚房便充滿了冉冉上升的蒸氣,白色的煙霧把她的視線引領到窗外,那裡也有一個緩慢地向上飄浮的男人。她不願意承認那是他,但那個穿著深藍色斜布褲和格子上衣的身體,確實是她所熟悉的。
她也無法尖叫,只是撲向窗子,把上半身伸出窗外,企圖及時攫住他的腳尖,但那裡有著她無法克服的距離。她只能以目光抓著他,緊緊地盯著不放,甚至不敢挪動身子,生怕最輕微的變化,也會使他立即消失不見。可是無論任何人或事情,也難以阻撓他飄遠的速度和方向,不久,在她眼前的他便愈變愈小,最後,他的軀幹被樹木、燈柱和大廈共同遮蔽。
「他好像還沒有醒悟,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變化。」她試著解讀最後看見他的神情︰「他的眼光並沒有投向我,只是又茫然又惶恐地落在四周和自己的雙手之上。那個本來平靜的下午並沒有任何改變,空氣中有陽光的氣味,而鳥在低叫。」她說。那天,她的身子一直掛在窗框上,直至夜色降臨,她卻聽不到水早已燒開了的尖銳聲響。從那時開始,她害怕夜。
過了半晌,當她回過神來,便會轉過頭去,以溫柔的語氣安慰阿鳥︰「不過,許多研究已經證實,飄蕩症並非通過遺傳而來,那很可能是一種基因突變,或由非常罕見的過敏狀況引發,也有可能是難以追尋的心理因素造成⋯⋯」她的聲音漸漸低沉下去,直至和空氣中的靜寂混合在一起。
阿鳥不忍揭破她,那其實就像肌肉萎縮症、神經纖維瘤或早發性癡呆般難以預防,也無法根治。要是飄蕩症患者走到公共醫院的診療室,向醫生訴說自己的早期症狀,其實醫生跟病人一般無助。她可以設想,醫生會給病人開出像糖果那樣的安眠藥,然後對他們說,保持心境舒暢是對抗任何疾病的不二法門,但他心裡明白,沒有任何人能避免病發。
醫生跟病人的不同之處只是在於,他以一直信靠的幻象保持定靜,要是人們想要待在安穩的生活裡,便要假裝使他們無能為力的問題並不存在,而為了維護僅存的假象,沒有人願意說穿這一點。
阿了早已沒有再到醫院去。
*
門被打開了以後,阿鳥看見賣氣球的男人打開了一個桃紅色的衣櫥,衣架上繫著許多晃動不定的氣球,其中一個繪上了老人的臉,張得老大的嘴巴裡藏著一個森林。她還來不及走進去,他已把氣球拔了下來,綑在她皮箱的把手上,打了一個死結,又把一根魚絲拴著她的手腕,魚絲的另一端連著他的掌心。他走向陽台,使她不得不跟隨他的步伐,那魚絲隨著男人的動作而揪著她手腕幼嫩的皮膚,來回的節奏像一種隱密的語言。
她走到陽台,欄杆抵在她心臟附近,街上黑壓壓的身影彷彿已經匯集成一道受了過多汙染的河流,而鳥不斷掠過天空,牠們連群結隊,從天空的一端飛到另一端,在大廈的頂部稍作停留,再一起飛到某個未知的地方。她知道,當鳥群隱沒在樹之中,而人們把自己藏在單位之內,夜色便會完全閉合,並在許多身體之內產生各種根本的變化。於是在夜裡,人們的身體更容易服從傾斜的本能。
阿鳥本來預期,賣氣球的男人會像牽扯著一個容易丟失的氫氣球那樣,把飄蕩者緊緊地拴在掌心。有人說,到了晚上,當火車站最後一班列車駛出了車站以後,他便把特製的魚絲,逐一套在那些步伐不穩的人手上,把他們送回家裡。也有人說,他只是依仗賣氣球的行銷手法,其實並沒有醫護和駕駛的知識。另一些人說,那是他在失眠的夜裡排遣時間和苦惱的方法。她無法印證這些說法的真偽,只是魚絲使她想起不同材料製成的繩子。她曾經在每個假日,騎著單車,在周末的露天地攤和編織店子之間來回穿梭,把每一款繩子握在手裡掂量,售貨員的頭臉總
是從貨物之間探出來問她,打算把繩子作何種用途,而她只能微笑。
當她坐在一輛行駛中的單車,她的腦子裡滿滿的都是被編成了一塊的繩梯、紮駐在帳篷下,或把船隻緊靠在碼頭的繩子。可是當她回到家,只是在每個午夜重複地遵從阿了的指示,把她的身體綑縛在藤製的搖椅上。白天,阿了在製作地圖的辦公室上班,在眼皮塗上淺藍色的眼影,偶爾打一個電話給友人,以輕快的語氣聊天。只有當夜色向著各個不同的方向蔓延,沉澱在她的身軀深處的倦意便像一朵吃人的花肆意地盛放。她失去跟阿鳥談話或在自己身上縛一個結的力氣,而只有在身體被嚴嚴實實地纏著,缺乏活動空間的情況下,她才能毫無防備地放鬆身上所有的肌肉。有時候,她會迅速墮進靜謐的夢裡,但更多的時候,她遺失了意識,便胡亂揮動憤怒的四肢,許多次,阿鳥以為,那張繩網快要被掙破,可是當她把頭湊上去,在繩子和繩子之間的空隙,卻看見阿了的眼睛緊閉,眼皮下的眼球快速地轉動,臉上有許多深深淺淺的紋路隨著她的表情泛起或消隱。阿鳥認為,那些她以不同的方式走過的路和穿越過的體驗,已成了線狀的痕跡,烙在她的皮膚上。
但日照會再次出現,把屋子占據,阿鳥必得在她轉醒之前,以鋒利的剪刀劃破結實的繩網,偽裝那樣的夜從不曾到來。不同材質的繩子鋪展在阿鳥面前像一條向前蜿蜒的路徑。她小心翼翼地維護那繩網,每天深夜編織而在清晨拆毀,她不敢想像,要是其中一根線斷掉造成一個孔洞,而那孔洞向四方八面擴大,她和阿了會陷入哪一種境況之中。她認為,那張網把日和夜的阿了分隔。日間的阿了,和夜間的阿了,因而長期處於各不相干的安穩之中。
*
阿鳥注視著天空,直至夜色把所有事物密不透風地包裹其中,她才看見賣氣球的男人筆直地站立,像一根牢固的木樁。她曾經遇上許多醫生,給她開出不同顏色的藥丸,當他們發現,藥物在她的身體裡,並沒有發揮意料之中的療效,便會表現出難以掩飾的失望和焦慮,因此,她「你知道,飄蕩是一件怎樣的事嗎?」阿鳥問。
賣氣球的男人心頭便緊了起來,這句話把他拋擲到一個警覺的狀態之中。他遇過許多病患,為了免卻自己被猜疑折磨,轉而希望身邊的人能通過他們層出不窮的測試。他不由得再看她一眼,發現她正在端詳著夜色,神情有一種過分的專注,另一個念頭出現在他的腦袋︰那其實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種想要傾吐的欲望。他便抿著嘴唇,等待一切隨時發生。
「最初,只是變得比較善忘。無法被緊記的事情像皮屑那樣紛紛脫落。」很長的靜默以後,她才說出一句話。「漸漸的,判別事物的準則變得不確定,方向感會出現障礙,有時候,甚至不知道,想要走的路究竟在哪裡,然後,身體會愈來愈輕,雖然重量並沒有一點改變,但可以感到,內裡一些重要的東西,那用以維持平衡和重心的元素,正在一點一點地流失。每天清晨,從夢裡醒來,也可以清晰地感到,那又少了一點,每天都比之前的一天減少了,但,卻做什麼也沒辦法阻止。四周的人的臉面,輪廓仍然相同,卻逐漸遙遠,直至某一刻,身體終於不受控仔細地端詳賣氣球的男人的臉,像禿鷹搜索地上的食物,尋找任何容易苦惱的跡象,不久以後,她卻認定了他是個潔癖者,擅於把不同的情緒分門別類地貯藏。
制地飄起來。」
「這是通過正式的研究所得出的資料嗎?」賣氣球的男人知道,適當地打斷病者的陳述,有助阻止他們過分沉溺疾病。「關於飄蕩症的研究寥寥可數。」阿鳥搖了搖頭。「因此,每一個飄蕩症患者的經驗都無法被取代。」
「可以看見和被界定的,畢竟比看不見和無法名狀的症狀更幸運。」為了避免陷入爭論,他試圖把話題繞到另一個方向去。
但她接著說,第一次發病的時候,在夜裡,當時針指向十二,她的身子朝東方晃蕩,彷彿屋子裡突然颳起了颶風,可是,無論家具還是坐在沙發上的人,都以原來的姿勢停留在原來的位置,只有她無法自控地撞上了天花板、牆壁,或一扇來不及掩上的門。她捲起衣袖和褲管,讓賣氣球的男人察看她手臂和大腿上顏色鮮嫩的傷疤。
可是賣氣球的男人只是盯著她那雙因為睡眠不足,而看起來充滿哀愁的眼睛。「失去重力並不可怕。」他以冷靜近乎淡漠的口吻說︰「無法適應飄蕩狀況的人,只是因為還沒有找到新的步行方式,掌握一種可以控制的節奏,以及在無法挽回地向上飄浮之前,抓緊可供依靠的關鍵點。」
關鍵點,阿鳥反覆地啄磨這個詞語,不久後,她的腦子裡出現了白的手。
那雙柔軟而白皙的手,曾經在每天早上,以溫柔的力度把辛辣的藥酒,揉搓遍布在她四肢因碰撞而產生的瘀傷之上,那使她感到痛澈心脾,但白說,那是一個必需的療癒過程。那些令她惴惴不安的夜,屋內只有白。她恍如機件故障的客機,被各種氣流牽引而衝向家具的尖角,書桌、冰箱、空調和衣櫥便都成了可怕的陷阱,只有白伸出手,竭力拉扯著她以減低衝力。她深信,那雙手除了拯救她,再也沒有別的意圖。
然而當他冰冷的指尖觸及她的皮膚,她還是感到自己罝身在偌大深邃的海洋,無論她如何努力協調手腳,還是無法掙脫遇溺的危險。
「他的手並不是一根可靠的繩子。」有一把篤定的聲音在她的腦裡冒起,作出這樣的結論。但她隨即感到驚訝,不相信那輕蔑的想法來自自己的腦袋。於是她把視線再次集中在墨黑的天空,而且相信藏在那裡的使人難以承受的黑暗,已經悉數掉落在她的身體之內。
飄蕩
街道仍然繁華,像一鍋煮沸過久的開水,已經容不下任何多餘的事物。賣氣球的男人常常在正午把頭探出陽台俯視著街上密密麻麻緩緩蠕動的黑色頭顱,總是感到街道在離他太遠的地方。他可以想像,在那裡,人們已經習慣了自己的身子,被擠壓在眾多陌生而黏膩的肉體之間,當他們抬起頭,發現天空被高聳的建築物切割成細碎的小塊時,並不會感到驚訝,他們更不會介意,再也沒有任何鮮豔的氣球,偶爾在上空飄過。然而總有一些什麼,會阻止賣氣球的男人隨著想像逸出那工作室的軌道。例如頻繁地響起的電話,他並不樂意拾起那聽筒,他知道,
張...
目錄
一 飄蕩
二 蝴蝶
三 勒貝度
四 顯影
五 玻璃界
六 放風
一 飄蕩
二 蝴蝶
三 勒貝度
四 顯影
五 玻璃界
六 放風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